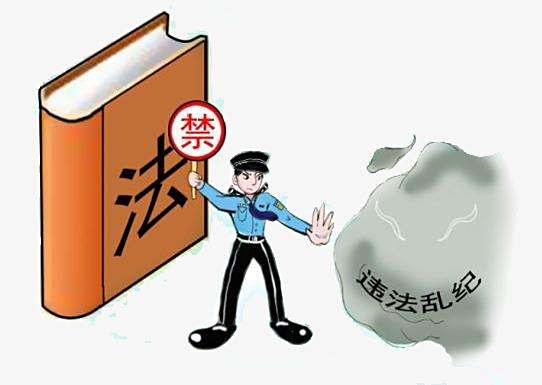
刷赞行为,即通过技术手段、人工操作或第三方服务虚构社交媒体点赞数据,本质上是对数据真实性的系统性扭曲,其性质已超越简单的“流量造假”,而是涉及民事侵权、行政违法乃至刑事犯罪的复合型违规行为。在数字经济深度渗透社会生活的当下,点赞数据作为用户反馈的核心指标,直接影响内容传播、商业决策与市场信任,刷赞行为对数据生态的破坏力持续加剧,其法律责任边界也需从多维度厘清。
刷赞行为的性质核心在于“数据欺诈”与“不正当竞争”的双重叠加。从数据要素视角看,点赞数据是用户真实意见的数字化表达,具有公共属性与商业价值。刷赞通过虚构数据稀释真实信息的权重,违背《民法典》确立的诚信原则,侵害平台、用户及经营者对真实数据的信赖利益。在商业领域,刷赞直接构成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八条规制的“虚假宣传”:商家通过刷赞虚构商品或服务受欢迎程度,误导消费者决策,破坏市场竞争秩序;MCN机构、网红为获取流量变现而刷赞,则构成“组织虚假交易”,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。此外,刷赞行为常伴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(如非法获取用户账号、密码用于批量操作)、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(如利用外挂程序篡改平台数据)等关联违法,性质呈现复杂化特征。
民事责任是刷赞行为最直接的法律后果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一十九条,数据权益受法律保护,刷赞导致数据失真,平台可依据服务协议追究用户违约责任,如限制功能、封禁账号;消费者因刷赞误导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,可依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五十五条主张“退一赔三”;若刷赞行为损害经营者商誉(如恶意刷差评后反向敲诈),被侵权方可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,要求停止侵害、赔偿损失。值得注意的是,刷赞服务的提供者与需求者需承担连带责任——刷手明知违法仍提供服务,商家明知数据虚假仍购买,双方共同侵害了平台数据管理秩序与消费者知情权,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常根据过错程度划分赔偿责任比例。
行政责任层面,刷赞行为面临市场监管部门与网信部门的双重规制。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二十条规定,经营者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,或者组织虚假交易的,监督检查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,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,并可吊销营业执照。《电子商务法》第十七条亦明确,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,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,欺骗、误导消费者。刷赞行为若通过电商平台实施,平台未履行审核义务将面临《电子商务法》第八十二条的处罚(最高罚款二百万元);若利用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批量刷赞,则违反《网络安全法》第二十七条,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,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。
刑事责任是刷赞行为的“高压线”,当行为规模、危害程度达到法定标准时,将构成犯罪。实践中主要涉及三类罪名:一是非法经营罪,若刷赞形成产业链,通过“刷单平台”“外挂程序”等方式牟利,非法经营数额达到五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,可依据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追究刑事责任;二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,刷赞过程中非法获取、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(如社交媒体账号、手机号),情节严重的(如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信息条数五千条以上),触犯《刑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;三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,通过技术手段侵入平台服务器篡改点赞数据,后果严重的(如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三十次以上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万元以上),构成《刑法》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犯罪。近年来,多地已宣判刷赞刑案:2022年浙江某科技公司因开发刷赞软件并牟利300余万元,主犯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,并处罚金;2023年江苏某网红团伙为带货刷赞,非法获取10万条用户信息,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。
当前刷赞行为的治理面临技术迭代与法律适用的双重挑战:一方面,AI换脸、虚拟账号、跨境服务器等技术手段使刷赞行为更隐蔽,传统基于IP地址、设备指纹的识别方式面临失效;另一方面,数据权属界定、平台责任边界、损失计算标准等问题仍需细化。例如,平台算法推荐机制是否对刷赞行为构成“间接帮助”,需结合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“避风港原则”与第一千二百条“红旗原则”具体判断;消费者因刷赞误导主张赔偿时,如何量化“虚假宣传”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,仍需司法实践探索。
刷赞行为的治理,需构建“法律规制-平台自治-技术反制-社会监督”的四维体系。立法层面可考虑将“数据欺诈”单独入罪,明确刷赞行为的刑事责任量化标准;平台应完善数据审核算法,建立“异常点赞识别模型”,并落实用户实名制与技术溯源机制;用户需树立“数据诚信”意识,拒绝参与刷赞交易;监管部门则需加强跨部门协作,对刷赞产业链实施全链条打击。唯有让真实数据回归价值本位,才能保障数字经济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,让每一次点赞都承载真实的民意与信任。